|
澳洲金融时报:澳洲大学学位现在还值不值?钱去哪儿了? 现在有四分之三的澳洲人觉得大学学位“不值”。他们的感觉到底对不对? 一旦谈到“要不要读大学”,很多人会觉得这笔账已经“算不通”了。 自2021年以来,学费涨了20%到50%;毕业生起薪停滞甚至下降,而且这还是对那些能找到工作的学生而言;有30%的毕业生在毕业六个月后还没找到工作;更糟的是,许多学生为了维持生计,不再花钱社交,教室变得空空荡荡。 难怪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在9月发布的调查显示,只有27%的澳洲人觉得学位“非常有价值”,有76%的人认为学位“太贵”“不值得”。 此外,人工智能的崛起也让大家怀疑:等到毕业证上的墨水干了,手里的文凭还有多少价值? 那真正的数字告诉我们什么?公众认为学位贬值,这种看法对不对?还是说读大学仍然是你往上爬最稳的一步? 在高中毕业生为2026年的入学选择专业时,《AFR》深入挖掘政府数据,看看过去10年毕业生的工资和就业情况到底怎么变化。 薪资发生了什么变化? 政府数据的分析显示,在传统热门领域,比如银行与金融、法律、计算机科学和医学,毕业生起薪在过去十年里按实际购买力计算基本停滞甚至下滑。 牙医学、护理学和经济学毕业生的起薪也在下降,而与此同时,学费飙升,毕业生平均背着约2.76万澳元的学生债,有些人远远不止这个数。 墨尔本莫纳什商学院(Monash Business School)高等教育政策教授诺顿(Andrew Norton)说,在未来十年,一般性的“宽口径”学位就业前景会比较暗淡。 他说:“我比较担心那种通用的商科学位、通用的文科学位、通用的理科学位,这些都有可能是风险相对较高的选项。” 澳洲教育部自2015年开始进行QILT(Quality Indicator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调查,按学科统计毕业六个月后,毕业生在薪资等多个指标上的表现。 结合澳洲央行公布的通胀数据来看,整体而言,本科毕业生在毕业后六个月的平均薪资,实际购买力大致守住了水平。 也就是说,扣除通胀对购买力的侵蚀后,薪水大致没缩水。 事实上,按照通胀调整后,2024年本科毕业生的薪资中位数比2016年高了1.7%。 诺顿(Andrew Norton)说:“在毕业生数量一直增加的情况下,薪资能维持大致稳定,其实已经是个不错的消息。” “如果最糟糕的情况真的发生,我们会看到薪资大幅下滑。但目前我们并没有真正看到这种情况。” 这一切的背景,是社会上愈发热烈地讨论:在工党政府设定的大幅提高大学学历人口比例的目标之下,大学的价值到底几何。 在新冠疫情期间的2021年,本科课程的本地学生入学人数曾达到29.1万人高峰;之后在2022年急剧下滑,2023年再跌至26.2万,创下十年来新低;2024年才小幅回升到27万。 诺顿认为,毕业生起薪停滞,并不一定说明学位“贬值”,反而可能反映大学学历在澳洲劳动力市场中已经变成一种“常态”。 澳洲统计局数据显示,在2014到2024年间,不管毕业多少年,本科学历人群的平均工资按实际购买力计算,小幅下滑,不到1%。 同期最低工资的涨幅比通胀高出9%,这意味着最低工资与大学毕业生之间的差距也略有缩小。 从整体人口来看,没有任何一类人的购买力在2024年出现明显下滑,某些最低薪族群的状况甚至在技术意义上更好了一些。 这个趋势在分专业数据上也能看出来。 按实际购买力计算,机械工程毕业生起薪下降了2%;银行与金融下降1.7%;法律下降1.3%;计算机科学下降1.6%;医学下降1.2%。牙医、护理和经济等专业的起薪也有所下滑。 但另一方面,一些总体收入水平较低的职业,比如兽医、航空航天工程师以及文学专业毕业生,他们的起薪按实际购买力反而涨幅靠前,分别增长9.2%、8.7%和7.8%。 当然,起薪并不能完全反映一生的收入潜力。比如QILT数据显示,刚入行的律师起薪可能比中学老师还低(前者约7.53万澳元,后者8万),但律师的收入成长空间要大得多。 不过总体来说,毕业生起薪相对于通胀仍在“守住阵地”。如果只从起薪来看,“学位价值大幅缩水”的公众印象其实是不准确的。 是不是读大学的人太多了? 虽然疫情之后三年里,本科新生入学人数有所下降,但拥有本科学历的劳动力总数依然在快速增长。 2016年人口普查显示,拥有学士或以上学位的人接近420万,占人口的17.5%;到2021年,这个数字已升至550万,占比21%。 简单说,劳动力市场中的大学毕业生数量从未像今天这样多。 多年来,联邦政策也一直在推动更高的大学毕业率。 阿尔巴尼斯政府在2022年启动了“大学协议”(University Accord),一项价值数百万澳元的高教领域综合审查,关注质量、负担能力和可持续性。审查报告提出目标:到2050年,要让55%的25至34岁澳洲人拥有大学教育背景。 诺顿多年来一直质疑这个目标不现实,甚至不必要。他说:“政府最近在公开场合已经很小心,不再反复强调这个具体数字。” “我觉得,有不少人读了大学,最后从事的是一份只需要12年级毕业或TAFE资格证就能做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大学学历带来的‘溢价’根本没有出现。” 诺顿指出,关于“55%目标”的官方说法,这几年已经变得模糊。政府现在更倾向于说这是一个“高等教育毕业目标”,可以理解为包含TAFE等非大学学历。 不过,即便对是否需要进一步大幅提高本科学历比例存在疑问,眼下的就业市场看起来仍能消化大部分我们培养出来的毕业生。 如果看就业结果,也就是毕业生在自己专业找到全职工作的比例,可以发现,在这八年的数据里整体趋势是上升的,只是在2023到2024年之间出现了一次明显回落。 在经历2020年新冠冲击导致的低谷(68.7%)之后,2023年有79%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在毕业后六个月内拿到全职工作,创历史新高。2024年这数字退回到74%,但依然高于疫情前70%到73%的水平。 所以,即便市场上充斥着大学学历候选人,读一个学位依然能在求职上维持与过去十年差不多的“保障度”。 当然,有些专业的“赌注”比其它专业更划算。 生物科学毕业生和建筑师是最不容易在本专业找到全职工作的两类群体(两者都是57.5%)。新闻和传播专业毕业生的表现也不算好,就业率只有58.5%。 相反,即便2024年相较2023有所回落,多个医疗保健专业的毕业生仍有很高的机会在本专业找到工作,从职业治疗(95.3%)到医学(91.3%)都如此。新毕业的工程师和教师同样高度“抢手”,就业率都远超80%。 会计(86.7%)、银行(82%)和商科(81.4%)毕业生目前看来也还算是“不错的选择”。 不过,考虑到这些行业受到自动化影响较大,这种有利局面在未来也可能发生变化。 人工智能会带来什么影响? 对于大学文凭的价值,另一大不确定因素就是人工智能到底会如何改造,甚至取消某些工作。 许多人担心,等自己刚毕业,手里的学位已经“过期”。 乔布斯与技能澳洲(Jobs and Skills Australia)执行董事克利夫·宾厄姆(Cliff Bingham)所在的独立政府机构,今年做了大量细致模型分析,逐项拆分各种工作里的任务,看自动化的影响有多大。 他说:“即使企业和个人充分利用所有自动化机会,我们也估计只有约4%的劳动者,他们的整份工作高度暴露在自动化风险之下。” 他认为,更普遍的情况是“人工智能辅助”,也就是人继续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只是大量借助AI工具。 今年社会舆论里有不少对“自动化冲击入门岗位”的恐慌,但宾厄姆(Cliff Bingham)说,数据并没有真正支持这种说法。至少目前来看,即便是在数据录入、呼叫中心这类“高暴露”岗位,入门级职位仍然“比较稳定”。 不过,宾厄姆也承认,就算做了这么多模型,AI本身还是一个“不断移动的目标”,未来的全貌仍不清楚。这种不确定性也在影响人们对未来某些学位在就业市场中价值的看法。 学生债务是不是改写了成本收益?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获得一个大学学位需要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 前莫里森政府在2021年推出了“工作就绪毕业生”(Job Ready Graduates)政策,大幅改变了许多专业的学费结构。以法律为例,学生每年自付学费从2016年的1.044万澳元涨到2024年的1.6992万澳元,实际涨幅接近21%。传播学学位的费用在实际价值上更是飙升了超过53%。 相反,数学或农业学位的自付成本按实际计算则下降了145%和155%。 根据Bankwest Curtain经济研究中心(Bankwest Curtain Economist Centre)的分析,学生贷款平均余额从2005年的8500澳元涨到2024年的2.765万澳元,增幅超过225%。 生活成本持续上升也意味着,即使你拿到了学位,在本专业找到工作,要达成“稳定甚至舒适”的财务结果,感觉也越来越不确定。 西悉尼大学校长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在8月的高等教育峰会(Higher Education Summit)上接受《AFR》采访时说:“我想,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他们会觉得社会契约已经破裂了。” “现在已不再是那种‘你在高中、大学都很努力,就一定能找到一份好工作,组建家庭,买得起房子’的时代了。” 威廉姆斯指出学生贷款大幅增加是其中关键一环: “有人读一个文科学位,欠下5万澳元以上的债,而其中很多人一辈子都还不完,这又会影响他们申请房贷、组建家庭的能力,他们本来也买不起房。我认为,对这些人来说,这真的是一笔很不划算的交易。” 教室空了,大学生活还值不值? 政府改变大学资助方式的决定并不是随机为之。当时莫里森政府就强调,这项政策是为了引导学生选择更明确对应就业岗位的学位,而不是“宽泛的人文教育”。 这也正式把社会对大学的看法往前推了一步: 大学不再被视为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各种非学术成年技能的场所,而更像是获取某种特定职业资格的“打卡步骤”。 墨尔本商学院管理学主席萨姆森(Daniel Samson)教授说:“对大多数人来说,读大学的目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三十年里,社会观念一直在从“大学是拓展思维、成长成熟的地方”,转向“大学是通往某个具体职业的工具化路径”。 他说:“在科学、工程、法律、医学和商科领域尤其如此。它们就是一张工作入场券,仅此而已。” 一边是观念改变,一边是经济压力。边读书边打工的大学生比例几十年来稳步上升。上世纪80年代,不到三分之一的大学生在读书期间工作;到世纪之交,这个比例上升到40%以上;疫情后基本稳定在65%左右。 诺顿说:“可惜的是,我不知道有哪项研究能用统计方式对比过去和现在学生的社交体验。”不过他同意,学生对大学的看法确实变了。 “很简单的算术是:现在很多人在线上学习,同时每周还得兼职20个小时左右,这样一来,他们留给和同学社交的时间就远远少于以前。这肯定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即使我们很难精确量化。” 萨姆森认为,这种观念改变,叠加新冠推动的线上教学加速,让许多大学校园变得像“鬼城”。 如果你只是想拿到一张学位证,可以在卧室里对着电脑上课,再配合打工排班,完全可以做到。但你也因此错过了以往很多人最看重的大学生活中的社交部分。 如果把大学教育中的社交和个人成长价值全部剥离,那就很能解释为什么如今大家对大学这“整套产品”普遍感到失望。 萨姆森回忆说: “我刚上大学时,大学生活就是我的全部生活。我的学习、体育、社交,全都在校园里,从黄昏到黄昏,有时甚至从黎明到黎明。” “而现在,我们有那些巨大的教室,却大多是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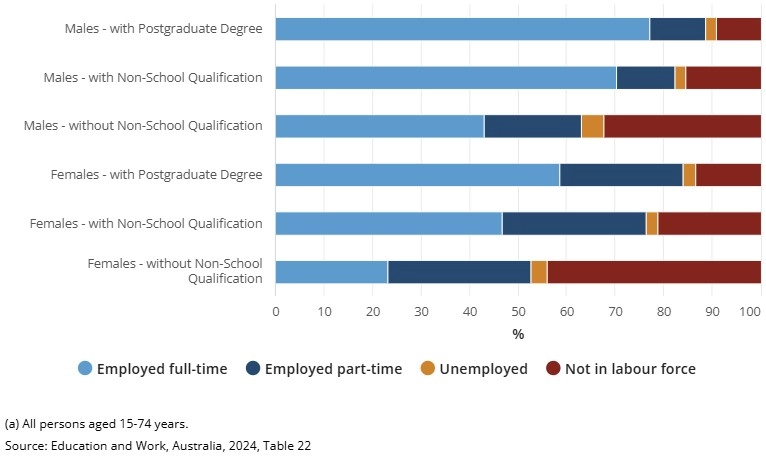 来源: https://www.afr.com/work-and-car ... ney-20251113-p5nfae Rachael BoltonWork and careers reporter Nov 30, 2025 – 12.00pm |